書展講座紀錄|余華幽默解讀「躺平」 冀年輕人走寬廣的大路

【點新聞報道】暌違三年,2023香港書展也重啟講座環節,整個書展期間,將有超過70場講座讓讀者和作家見面,吸引了大批本港和外地的讀者前來「朝聖」。著名作家余華的講座昨日(22日)舉辦,場上笑聲連連,余華老師更是金句頻出,其中不乏對當代青年受用的觀點。點新聞記者整理講座精彩談話,供讀者回顧收藏。
問:最希望哪一部作品被討論?
余華:其實我所有的作品都很值得討論。出於今天的特殊情況(講座被分為上下兩場),所以我覺得應該討論《兄弟》,因為《兄弟》有上下集。
問:創作成名作《十八歲出遠門》,有沒有什麼念想?
余華:小說就是一個寫作,和人的經歷是一樣的。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。當時是1986年,我要去參加北京文學的筆會,那個時候我作為一個青年作者還沒有出名,天天想出名但是還沒出名,就是這樣的階段。當時不知道寫什麼,看到杭州的《錢江晚報》有一條(新聞),說有一輛裝蘋果的車因為出車禍,車上蘋果被搶光,受這個啟發,寫下開頭「柏油馬路起伏不止,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。我走在這條山區公路上,我像一條船。」
拿到北京以後,遇到貴人李陀,李陀看完對我鼓勵很大,說「你現在走在中國文學的最前面」。從那一刻突然發現,我走在最前面。現在回頭看,我確實不能說在最前面,也是最前面之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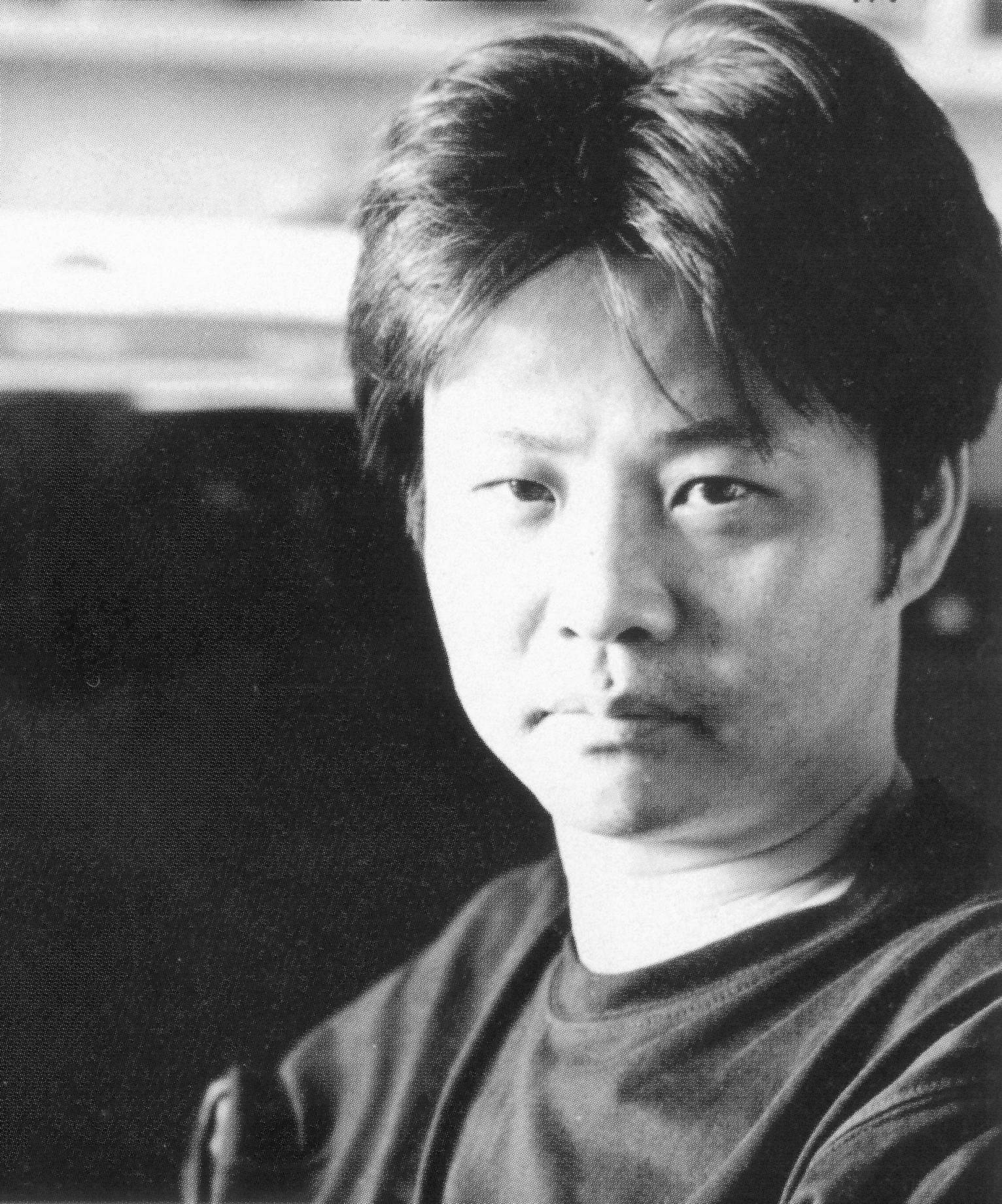
問:創作《活着》的時候遇到瓶頸?
余華:《活着》準備了很長時間,想寫一個人和他命運的關係,但是一直不知道從哪入手。有人曾問靈感是怎麼產生的,其實靈感每天都出現,問題是是不是準備好了,如果沒有準備好,靈感會迅速出現又更快地消失。只有準備好了,靈感來了才是靈感。《活着》屬於一直在想,故事細節都有,不知道如何下手。一天午睡中,突然想到「活着」兩個字,覺得這就是小說的書名,馬上感覺來了,就開始寫,很順利。
問:《兄弟》的時代背景有何考量?
余華:也算是一個機遇吧,其實我1997年的時候已經開始動手寫了,97年的時候我已經感覺到我們中國出現了很大很大的變化,但是我當時沒寫完,我覺得是命運對我的安排。一直到了2003年,我重新開始寫。
現在看來,97年的時候感受到的巨大的變化,到了04、05年的時候,你覺得97年的變化根本不大,04、05年才是真正的巨大的變化,所以我覺得這是,怎麼說呢,我命好,就讓我在03年才開始真正的去寫它,而不是97年就完成。
問:您曾經把創作作品分三個階段,這個《文城》會不會是您的第四個階段?
余華:我對我自己的寫作的要求其實很簡單,第一是不要重複自己,因為重複自己,我自己都沒有興趣。第二就是我給我自己的長篇小說,拉出一個質量的平均線,我自我感覺達到這個平均線了,就可以拿出去出版了,如果達不到的話,繼續擱在那慢慢來。
問:您的作品中男性形象都特別完美,是不是在刻意美化男性呢?
余華:無意之間美化男性。在文革這個時代,跟今天這個時代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文革時代,在外部環境很壓抑的情況下,家庭的內部非常團結。我從小到大一直到文革結束,我就沒聽說過我們鎮上有人離婚的。現在,十多年前,我就已經掌握這個經驗了,遇到一個幾年沒見的朋友,千萬不要問你先生怎麼樣,或者是你太太怎麼樣?我記得有一次問,背後有人踢了我一腳,我才反應過來,人家早就已經分了,但我確實不知道,因為分了也沒告訴我是吧,沒有必要告訴我。
我的《活着》和《許三觀賣血記》這兩個小說,翻譯到英文的時候在美國好多出版社退稿,只有一個出版社的編輯給了一個理由,他是讓代理人來轉告這個問題,想要問我,他說為什麼你的小說裏邊的人物只承擔家庭的責任,而不承擔社會的。因為我覺得這真是一個文化差異,當然現在已經不存在這個問題了,但是在90年代,這依然是一個問題。所以我就跟他做了一個回答,說雖然我們國家歷史有3000年了,我們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他的位置,他只有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是有位置的,所以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紐帶的連接是家庭和家庭之間的連接,不是美國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連接。
問:余華老師,您的作品中有多少靈感,或者內容是來自於個人生活體驗?
余華:我不知道該怎麼說,比如說《兄弟》出版以後他們說余拔牙是我。我告訴他們要是余拔牙是我的話,我肯定把他寫成英雄人物了。但是確實他的那些拔牙的技術,我是擁有的。
問:在創作《活着》的過程中,對於主人公悲慘遭遇的刻畫是如何把握的,是更多的源於自身生活還是來自想象?
余華:因為我們經歷過極其貧困的一個時代,我們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。當然現在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的人還是很多。
我最早寫《活着》的時候,是用第三人稱的,用一個旁觀者的,還是延續了像《在細雨中呼喊》這樣的語言方式,就是那種比較優美的一種語言方式來寫。後來用了第一人稱以後很順利寫完了,所以我終於明白了就是,你要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看福貴的話,他除了苦難沒有別的什麼,但是你讓他自己來講他的生活的時候,很多人說福貴是一個悲劇人物,我就一直不同意,因為福貴是用一種幸福的口吻在講述他悲慘的一生。
從他自己來說的話,他認為他是很幸福。他有過世界上最好的妻子,有過兩個最好的孩子,他有過最好的父母,他最後晚年的時候回憶起來,所以他覺得自己的一生無悔。
人生是什麼,我說過很多次了,生活是屬於自己的感受的,不屬於別人的。
問:福貴的母親安慰他說,「只要活得快樂,窮也沒關係」,這是您的名言嗎?
余華:這確實是我寫出來的,但我覺得這個是福貴的母親說的,是她的名言。
問:你會因為自己筆下人物的悲慘境遇而難過嗎?
余華:初稿的時候感覺不那麼強烈,為什麼呢,因為讓我很難過的那一段,可能不是一口氣寫完的,可能是分成好幾天寫完。最難受是修改的時候,你是整段看下來的。
我印象中《兄弟》上部寫到最後的時候,我的桌子邊上擦眼淚的紙,還有鼻涕呢,一把鼻涕一把淚,沒有那麼高,但是也是一個小山坡。
問:有些情節您當初是怎麼設想的呢,就是要賺我們的眼淚嗎?
余華:任何一個作家,他在寫作的時候都要面對一個讀者,就是他自己。因為凡是有寫作經驗的人,哪怕你是給領導寫講話稿,或者是你寫年終總結,都是作者和讀者的雙重身份。
問:對於百度回答「余華是名優秀的牙醫,但蘇童是出色的作家」,您如何看待?您認為文學成就是可以比較的嗎?
余華:我和蘇童旗鼓相當,但是蘇童有一點不如我,因為他不會拔牙。

問:如何看待「把痛苦留給讀者,快樂留給自己」的說法
余華:這個我今年在澳門就已經更正了,我說我沒那麼缺德。我是把痛苦留給虛構,把快樂留給現實。因為當我把我那種痛苦的情感全部在虛構的世界裏邊表現出來以後,在現實裏邊,留給自己的就只剩下歡樂了,輕鬆無比。
問:作家筆下如何來刻畫人物?
余華:當一個人物剛剛來到作家筆下的時候,就好比是我剛認識的一個朋友一樣。隨着寫作的深入,對他的理解越來越深,越來越了解,當我寫到後面三分之一的時候根本就不用發愁他們會怎麼說話,他們絕對會說出他們自己的話來,不是我的話,是他們的話,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了,因為我已經完全理解這個人物。
問:《文城》故事背後有沒有趙氏孤兒的影子呢?
余華:一些小說家有時候跟一個村長差不多,管好多事情,詩人們相對來說,管的事情沒有小說家那麼多。小說家要給他們分配工作,失業以後還得再就業,所以沒有想到那麼多。
我始終有個觀念,文學最基本的一個事情,還是要與人為善,就是我們可以去寫一些醜惡的東西,但是我們也要在裏邊發現一些美好的東西。讓我們賴以能夠生存下來的,是我們人性中美好的東西,而不是那種惡的東西、醜陋的東西讓我們走到今天。
作為一個作家,應該去描寫那種惡的醜陋的,但是你必須要從裏邊寫出美好的東西來,哪怕是喬治·奧威爾的《1984》、《動物莊園》,我依然能夠從裏邊讀到希望。

問:請問您如何看待自己成為文化圈頂流這件事?
余華:我也不知道,當然我知道有很多讀者讀過我的書,這事我是知道的。這兩年確實我已經感受到,怎麼上街被認出來了,就是視頻太多了。
兩年前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在北京一個餐館吃飯,突然有一個朋友給我發個微信,說你上微博熱搜了,然後下面有1000多個人講他們自己的躺平故事,後來他們告訴我,剛好就是大家都想躺平嘛,但是可以理解,因為誰不想躺平是吧。而且退休是不是算躺平,退休也應該算躺平吧。所以如果退休是躺平的話,那我們可以認為躺平是一種社會制度,是允許的,是吧,有些人想早一點躺平,有些人想晚一點退休,想晚一點躺平是嗎,這都可以理解。

比如說後來小紅書上把我跟一個小狗合在一起,「潦草小狗」,我要是不在北師大當老師的話我都不知道。我的那些學生們天天看這個,然後都發給我。我覺得很好,我覺得很可愛,所以我現在髮型變了,看他們怎麼辦,哈哈哈。

問:您會用AI進行創作輔助嗎?
余華:我不會,我絕對不會用AI去創作,我想它會把我帶向黑暗。AI可能能夠表現出我們已知的所有,但是它無法表現出我們未知的。它能夠表達的就是人的看法,不是命運的看法。一個人的命運會怎麼樣,AI是無法來決定的。所以我們唯一還能夠保留我們自己的,就是我們對自己命運的不可知。
問:年輕人覺得自己充滿着束縛,如何在現在這個同時充滿束縛和自由的時代去面對這種困境?
余華:每個人所說到的束縛是不一樣的,有的來自家庭,有的來自單位,有的來自同事、同學、朋友,各種各樣。但是有一點我是知道的,就是當我年輕的時候,我的父輩們來指導我的時候,我是很反感的。
為什麼,因為我認為他們說的都不對,因為他們的經歷和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不一樣,他們的經驗對我們未必有用。老一代人總喜歡教育年輕的一代人,我們不需要他們教育。你們最清楚你們該怎麼做,你們現在是在到處摸索、在尋找出路。找到了就出去了,沒找到的繼續找。
我今天更正一下就是什麼呢,因為我在《兄弟》的結尾裏邊說到「窄門」,我要跟你們說的什麼呢,你們年輕的時候,千萬不要去走聖經所說的「窄門」,也千萬不要去走馬克思所說的崎嶇的小路,為什麼呢,那個路走過去基本上是走不回來的,先走寬廣的大路,人越多越好,等你們感覺到自己有一定能力了,覺得我可以去走一走獨木橋了,我可以去走一走「窄門」了,我可以去走一走崎嶇的山路了,你再走。所以你不要因為(我)余華沒有上過大學,莫言沒有上過大學,史鐵生沒有上過大學,(就得出結論)作家不用上大學,錯了。我當年是考不上大學,我考上我能不去嗎,所以這個是不存在一個榜樣作用的。
所以我還是希望,在年輕的時候,剛剛走上社會的時候不要走偏門,就走正道,覺得自己好像有自己的想法了,然後再走一下偏門,這個時候可能走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來,這是我的建議。
問:人一生的幸福是可以從苦難中獲取的嗎?
余華:當你面對苦難的時候,其實裏邊是有幸福的。但是能避開就避開,不要為了追求所謂的成功去經歷苦難,太多的人經歷了苦難以後依然沒有成功,現在這個世界最多的就是雞湯,但又喝不着,是假的。
問:您對諾貝爾文學獎有過期盼嗎?
余華:我寫作已經寫了40年了,我心裏很清楚了,就是當我不能把握的事情,想都不要去想。
如何寫好一部小說,如何把它寫得更好,這是我所能夠把握的,當這本書出版以後,能否受到讀者的喜愛,能否獲獎,這根本是我做不到的。而且我也不可能為了獲獎給某一個評委打電話吧,況且我也不會說外語。
(點新聞記者程園園整理報道)
更多閱讀:
書展講座紀錄|許知遠談兩代人眼中的香港 始於「中年危機」的傳記




